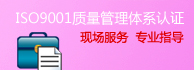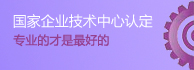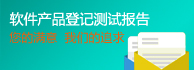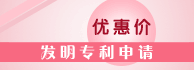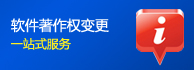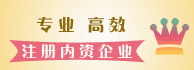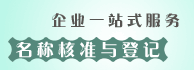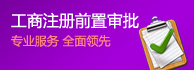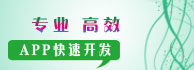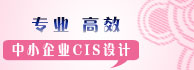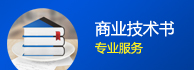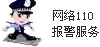微信文章
曾国藩:传统教育的“破壁者”与“守灯人”

在晚清教育困局中,曾国藩以“经世致用”为利刃,划破了传统教育空疏无用的桎梏,却始终紧握“修身立德”的灯盏,在革新与守成之间,走出了一条独属于他的教育变革之路。他的探索,既是对传统教育的修补,更是对近代教育的启蒙,成为连接古典与现代的关键桥梁。
曾国藩对传统教育的革新,首先始于对“教学内容”的颠覆。明清以来,科举取士主导下的教育,深陷“八股取士”的泥潭,学子埋首四书五经,专攻时文制艺,学问与现实脱节,成了“纸上谈兵”的空疏之学。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,提出“为学当以经世致用为要”,将教育内容从“纯学术”拉回“实用场”。他主张学子不仅要读“圣贤书”,更要学“有用之学”——在经史之外,增设天文、地理、算学、河工、漕运、兵法等实用科目,甚至鼓励子弟学习西方科技知识。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,他反复叮嘱“算学为六艺之一,不可不精”,还亲自为其挑选算学书籍,打破了“西学为奇技淫巧”的偏见。这种“兼容并蓄”的内容革新,让传统教育不再是封闭的“象牙塔”,而是面向现实问题的“工具箱”,为近代“新学”的兴起埋下了伏笔。
其次,在“教育方法”上,曾国藩摒弃了传统教育“死记硬背”“单向灌输”的刻板模式,转而强调“知行合一”与“因材施教”。传统私塾中,先生多以“棍棒”为教鞭,以“背诵”为唯一标准,忽视学子的个性与实践能力。曾国藩则主张“读书贵有心得,不贵徒有记诵”,鼓励子弟在读书时“勤思善问”,将书中道理与生活实践相结合。他自己便是“知行合一”的践行者:读《孙子兵法》,便在练兵中实践“知己知彼”;读《水经注》,便在治理河工时借鉴治水之法。同时,他针对不同子弟的禀赋制定不同教育方案——曾纪泽“性刚”,便教他“戒骄戒躁,涵养心性”;曾纪鸿“性敏”,便引导他钻研算学,发挥特长。这种“重实践、重个性”的教育方法,打破了传统教育的僵化格局,让教育从“培养书呆子”转向“培养实用人才”,为近代教育的“个性化”理念提供了雏形。
然而,曾国藩的革新并非对传统教育的全盘否定,而是“守其核心,变其枝叶”。他始终将“修身立德”视为教育的根本,坚守传统教育的“心性培养”内核。在他看来,无论学问如何革新,“做人”始终是第一位的——“读书志在圣贤,非徒科第;为官心存君国,岂计身家”。他在《曾氏家训》中反复强调“孝悌、勤俭、谨信、谦逊”的品德修养,要求子弟“每日三省吾身”,将道德教育融入日常点滴。即便倡导西学,他也坚持“中体西用”的原则,认为西方科技只是“器”,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才是“体”,不可本末倒置。这种“守正出新”的态度,既避免了传统教育的僵化,又防止了盲目西化的偏颇,为近代教育的转型提供了稳健的路径。
曾国藩的教育革新,本质上是一场“传统内部的自我突破”。他没有割裂历史,而是在传统教育的土壤中,植入了“实用”与“实践”的新种子;他没有抛弃文化根脉,而是在“修身立德”的根基上,搭建了“兼容西学”的新框架。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,他的探索不仅培养出了曾纪泽这样“学贯中西”的外交人才,更影响了后来的洋务派教育——京师同文馆、福州船政学堂等近代学堂的创办,都或多或少借鉴了他“经世致用”的教育理念。
时至今日,曾国藩的教育思想仍具启示意义:教育既要“守根本”,培养人的道德品格与文化素养;又要“谋创新”,适应时代需求,教授实用知识与实践能力。这种“守正与创新并举”的智慧,正是他留给后世教育最珍贵的遗产。

上一篇文章:
已经是第一篇了!
下一篇文章:
论做事之路气力